黑格尔(G. W. F. Hegel)曾说:“这样一种巨大的变革,即产生一位统治者,想必发生过两次。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是偶然发生的,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,一次算不上是一次。所以,奥古斯都的风格必定延续下来,拿破仑也必定两次遭到废黜”——[德]黑格尔:《世界史哲学讲演录》,商务印书馆,2015年,第357页。
后来,卡尔·马克思(Karl Heinrich Marx)于1844年1月在《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〉导言》中提及了他基于黑格尔历史反复思想的思考:“历史不断前进,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。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。在埃斯库罗斯的‘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’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,还要在琉善的‘对话’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?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”——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卷,人民出版社,1956年,第456~457页。
在马克思写于1852年的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中,他更简洁地阐述了这一思想:“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,可以说都出现两次。他忘记补充一点: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,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”——[德]马克思: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,人民出版社,2018年,第8页。在书的结尾,他作出一个预言:“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·波拿巴身上,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”——同上,第121页。而这个预言在1871年得到实现。马克思讨论了一个重要现象,即历史会生成惊人的反复。 日本现代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对历史的反复进行了分析:“所谓历史的反复并非意味着相同事件的重复。能够反复的并非事件(内容),而是形式(结构)。事件本身能够避免反复,但是,像周期循环那样的某种结构是无法避免反复的”——[日]柄谷行人:《历史与反复》,中央编译出版社,2018年,第4~5页。
关于历史的反复,马克·吐温(Mark Twain)的一句话很经典:“历史不会重复,但会押韵(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, but it does rhyme)”黑格尔的一句话常被误传:“历史总是在人们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之前不断地重复运动着(daß die Geschichte die Eigenheit hat, repetiert zu werden, so lange, bis die Lektion begriffen wird)”(也就是人们熟知的“人类从历史里学到的唯一教训,就是人类学不到任何教训”)于我而言,我更喜欢一个出处不明的说法:“历史是个有耐心的老师,你学不会,它会一直重复”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:“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,说到底,是要坚信事物前进发展的必然趋势,要坚信新生事物终将代替旧事物,要做新生事物发展的促进派。同时又要承认事物发展道路的曲折性,既要反对循环论,又要反对直线论,对事物发展的暂时倒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,不能丧失信心,自觉地按照螺旋式上升、波浪式前进的方式,把事物不断推向新阶段”——王伟光:《新大众哲学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。这种想法源于一种信心:“历史尽管有波折,但总体是前进的。”但它何尝不是“马克思主义作家以这种或那种装束表现出来的历史线性进步观点”——张文喜: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。
正如澳门大学教授王笛所说:“所谓的历史有规律、可以预测的说法,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。因为历史决定论,导致有些人认为,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,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。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‘宏才大略’的人,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。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,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。但是他们的追求,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,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,按照所谓自认为的‘伟大思想’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,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。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,不惜一切代价,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。就是哈耶克(F. A. Hayek)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(The Road to Serfdom)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(F. Hoelderlin)的话:‘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,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。’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”——王笛:《历史的微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。
卡尔·波普尔(Karl Popper)认为:历史决定论就是权力崇拜,“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”——[奥]卡尔·波普尔著,郑一明等译: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信心如钻石般珍贵,但抛开历史决定论带来的信心,我们的信心还可以从何而来?两段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的访谈将大有裨益:
……
罗新:对,这是一个时间尺度问题。如果放在两千年的尺度里看,进步就更加鲜明,两千年前绝大多数国家还是奴隶制,很多人口处在和动物一样的法律状态、人生状态,可是今天,至少没有合法的奴隶制了。而人类已经有二十万年的历史,如果放到现代智人的尺度里,两千年也是很短的时间段。
杨:可是人的寿命就是七十年或者八十年,那个尺度对于一个人来说,意义是什么呢?
罗新:最大的意义就是,我们一定要跳脱个体的生命尺度。个体的生命尺度,过去甚至只有二三十年。如果我们跳脱这种时间尺度,你会发现,作为一个种类的人,是有巨大变化的,而且变化速度越来越快,而且有一定的方向。过去,人们很讨厌说历史有方向,觉得决定主义特别天真,但是在某些意义上,我们觉得历史有方向。这些方向一定和人的本性有关,比如说,人类本性是向往自由的,任何人都向往自由,当然,任何人也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过得好,但是毕竟这些人要在一起过,所以最后要协商,协商的结果就是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平等地位。只要你接受了别人和你是平等的这个前提,最终自由一定会降临人间,这是人性决定的。在这一点上,我特别喜欢清华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写的《权利的形而上学》,那本书虽然没有明确写这句话,但我觉得(可以概括出来):自由是人的天性,人类实现自由是天性决定的。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的方向。……
罗新:对,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的心态跟你在今天的心态很像,就是对价值有强烈的渴望,而且对这个价值迟迟不能到来充满愤怒,因此就不相信了,突然就有了一种幻灭感。那个时候一说到这种幻灭感,我的眼泪就下来了,但是很有趣的是,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,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——吴琦主编:《单读33:多谈谈问题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·铸刻文化·单读2023年版。而在许知远《梁启超:亡命(1898—1903)》新书北京首发会上,罗新对时间感也从个人角度做出了深刻的表述:“在历史当中的人会觉得没办法熬这个事,熬不过去了。经过了1898年之后的屠杀之后的那些仍然倾向于改革的人,肯定觉得完了,从此就完了。他们谁也没有想到,要不了多少年,连清朝都不在了。你要看到这个事实,更不用说现在世界是很加速的。其实你以为熬不过去了,其实有人比你还熬不过去。所以不需要对眼前的黑暗感到焦虑、沮丧。时间过得很快的,而且很多你现在觉得不可能的变化会发生,很快就会发生。我是就个人角度说这个话”
马克思细致描绘了近代法国政治的不断下行:从共和国倒退回了帝国。法国的政治倒退和路易·波拿巴的不断上升仿佛不可阻挡,但马克思依然表现出了他站在历史尺度下的乐观:“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,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,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、关系和条件”——[德]马克思: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,人民出版社,2018年,第12页。马克思对其置身其中的近代世界的前途抱持一种历史性的乐观。这种乐观超出了理性,达于人类将走向美好未来的信念。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充满反复,但也不乏颠覆和变革。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,而是充满了必然性和可能性的交织。挑战在于理解这些历史的律动,怀着对自由和进步的信念,勇敢面对历史,迎接未来的到来,并在其中找到自身的定位。
诗疾默 你好果实君2024年03月11日 14:45河北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jqRmyjda17-35_gzLPF2lg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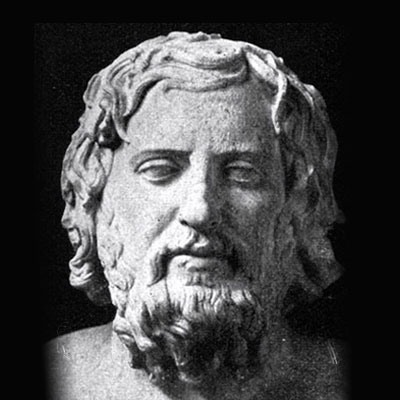
0